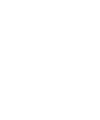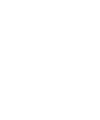影视诸天从流金开始 - 第1034章 大唐双龙传(熟能生巧)
竹舍内,茶香袅袅,方才那天变引发的紧张气氛,在易华伟云淡风轻的态度与温热的茶汤中,渐渐缓和下来。
然而,师妃暄与石青璇心底的震撼,却如水中涟漪,层层扩散,未曾止息。
又闲谈了几句关于音律、茶道的雅事,易华伟多是倾听,偶尔插言,却总能切中肯綮,发前人所未发,令石青璇美眸中异彩连连,只觉此人学识之渊博,见解之超卓,实乃平生仅见。
不知是否因方才那曲箫音勾起了沉淀的记忆,还是此刻与石青璇这等清雅之士对坐,触动了心弦,易华伟放下茶杯,目光落在石青璇置于石桌那管青翠竹箫上,温和开口:
“石大家箫艺通神,令人叹服。易某不才,昔日也曾涉猎丝竹,略通琴艺。今日秋光正好,雅室清幽,不知易某可有幸,借石大家宝地一用,取琴与大家合奏一曲,以酬知音?”
石青璇闻言,清澈的眸中顿时绽放出惊喜的光采。她一生酷爱音律,视若生命,但能与之在技艺与心境上平等交流者,寥寥无几。易华伟气质超凡,见识广博,他主动提出合奏,无疑是对她箫艺的最高认可,也勾起了她极大的好奇与期待。
“盟主过谦了。能得盟主赐教,青璇求之不得。”石青璇盈盈起身,语气中带着难得的欣然。
师妃暄也颇感意外,石青璇眼界极高,等闲之人连听她一曲都难,更遑论合奏。易华伟此举,无疑又将展现其不为人知的一面。她静坐一旁,准备凝神倾听。
不多时,石青璇抱着一架通体黝黑、造型古拙的七弦琴置于茶台上。那琴木质温润,隐现冰纹断理,琴弦如丝,一看便知绝非凡品,更带着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沧桑气息。
见易华伟坐下,石青璇收敛心神,重新执起自己的竹箫,玉立一旁,静候易华伟起音。
易华伟屏息静气,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搭在琴弦之上。闭目凝神片刻,当他再次睁眼时,手指微动。
“铮——”
一声清越的泛音响起,如同水滴落入深潭,打破了室内的寂静。随即,指尖流淌出舒缓悠扬的旋律。
琴音空灵旷远,初时如云卷云舒,风过松涛,带着一种闲适自在的意境;渐渐又如幽谷溪流,潺潺湲湲,清澈见底,映照着天光云影。
石青璇凝神倾听,捕捉着琴音中的每一个细微转折与情感流露。她发现易华伟的琴艺,并非追求繁复的技巧,而是直指音律的本源,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自然的道理,直叩心扉。她心中暗赞,不再犹豫,将竹箫凑近唇边。
一缕箫音,如同自九天垂落的月华,轻柔地汇入那潺潺的琴声溪流之中。箫声清冷幽婉,与琴音的温厚旷远相得益彰。起初,箫声只是小心翼翼地附和、点缀,如同月光追逐着流水的步伐。
但很快,石青璇便感受到易华伟琴音中那股包容万象的引力与无比稳定的节奏感,她放心地将自己的情感与理解尽情注入箫声之中。箫音时而高亢,如鹤唳晴空,与琴音中的松涛相应和;时而低回,如泣如诉,与琴音中的幽泉共悲欢。
易华伟的琴音始终如同广袤坚实的大地,承载着、呼应着石青璇那如云如雾、变幻莫测的箫声。他的指法娴熟无比,心念动处,音符已自然流淌,仿佛不是在“弹奏”,而是在“引导”着音律本身。偶尔会即兴加入几个精妙的变奏,石青璇总能心领神会,以更加出彩的箫音衔接上去,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
琴箫合鸣,水乳交融。
那和谐的乐声仿佛拥有了生命,在竹舍内盘旋升腾,勾勒出一幅超然物外的山水画卷:有崇山峻岭的巍峨,有茂林修竹的清幽,有清风明月的朗照,更有一种超越尘世、寄情天地的逍遥与淡淡的、看尽繁华的落寞。
师妃暄闭目聆听,只觉心神仿佛被这美妙的音律洗涤,诸多杂念尽消,体内《剑典》真气都似乎变得更加活泼灵动。心中震撼无以复加,易华伟不仅武功通玄,竟连琴艺也臻至如此化境!他与石青璇的合奏,已非技艺的比拼,而是心灵与境界的共鸣。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久久不绝。
竹舍内一片寂静,唯有窗外秋风拂过竹叶的沙沙声,仿佛也在为方才的仙乐伴奏。
易华伟缓缓收手,琴弦最后一丝震颤归于平静,抬眼看向石青璇,眼中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与愉悦:“石大家箫艺,已得自然之妙韵,能与大家合奏,实乃易某之幸。”
石青璇放下竹箫,绝美的玉容上因激动而泛起淡淡的红晕,更显娇艳不可方物。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澎湃,看向易华伟的目光充满了一种遇到真正知音的欣喜:“盟主琴艺,才是真正的‘近乎于道’。青璇以往所奏,不过是井底之蛙,今日方知音律之海,浩瀚无垠。多谢盟主指点。盟主唤小女子青璇便是,大家之名,愧不敢当!”
她这话发自肺腑,与易华伟合奏这一曲,让她对音律的理解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易华伟含笑摇头:“石大家过誉了,互相印证而已。”
此时,日头渐高,已近正午。温暖的秋阳透过窗棂,将室内映照得一片明亮。
易华伟目光掠过窗外那几株在秋阳下傲然绽放的秋菊,心中微动,复又看向石青璇那清丽绝俗的容颜,一个念头浮现。他温和道:“今日得闻仙音,又蒙青璇盛情,易某无以为报。若不嫌弃,易某愿为青璇描摹一幅小像,聊作纪念,如何?”
石青璇微微一怔,随即一抹淡淡的羞意染上耳根,但更多的却是惊喜。她虽不喜张扬,但女子天性,对描绘自身容貌之事,总难免有几分在意,尤其是由易华伟这等人物执笔。她轻轻颔首:“那……便有劳盟主了。”
师妃暄也颇感兴趣,想看看易华伟在丹青之道上,又有何等造诣。
石青璇取出了画纸、画笔与颜料。画纸洁白如雪,质地非凡;画笔粗细兼备,狼毫柔软;颜料更是色泽饱满,灵气隐现。
易华伟让石青璇依旧坐于窗边的蒲团上,姿态自然即可。石青璇依言而坐,手持竹箫,置于膝上,目光微垂,侧颜对着易华伟,窗外秋光映照着她的脸颊与发丝,仿佛为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身后是隐约的竹影与点缀的秋菊,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
易华伟静静观察了片刻,将石青璇那独特的气质、神韵,以及周围环境的意境,尽数捕捉于心。
随后,他执笔蘸墨,手腕悬空,落笔如风!
动作不再如烹茶、弹琴时那般温雅,反而带着一种剑客出鞘般的果决与精准。笔走龙蛇,挥洒自如,时而用细笔勾勒发丝衣纹,纤毫毕现;时而用泼墨挥写竹影背景,意态淋漓。
作画之时,易华伟眼神专注,仿佛整个心神都沉浸在了笔下的世界之中,周身自然流露出一股宗师气度。
师妃暄与石青璇都屏息凝神,生怕打扰到他。
不过一盏茶的功夫,易华伟便已搁笔。
“请过目。”
石青璇怀着些许紧张与期待,起身走近。当她目光落在画纸上时,整个人顿时怔住了,美眸圆睁,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撼。
画纸上,一位手持竹箫的青衣女子侧坐窗边,容颜清丽绝俗,神态安详中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孤寂,眼眸清澈,仿佛蕴含着万千言语,却又欲说还休。其神韵之生动,气质之传神,竟比她本人更添几分空灵意境。周围的竹影疏朗,秋菊傲霜,都与人物完美融合,整幅画不仅形似,更是神似,尤其抓住了石青璇那源自灵魂深处的清冷与灵秀,仿佛将她的魂魄烙印在了纸上!
画旁还有一行清俊挺拔的题字:“空谷幽兰,清音自远。——无名写于幽林小筑。”
这……这简直是神来之笔!
石青璇从未见过有人能将自己画得如此传神,如此……直击心灵深处。她看着画中的自己,一时竟痴了。
师妃暄也上前观看,心中惊叹不已。易华伟的丹青之术,竟也如此登峰造极!这幅画的价值,已无法用世俗眼光衡量。
“盟主……此画,青璇……”
石青璇抬起头,看向易华伟,声音微颤,一时竟不知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与震撼。这份礼物,太重了,重到她不知该如何承受。
易华伟淡然一笑:“喜欢便好。此画能得遇真主,亦是它的缘分。”
看了看天色,阳光已有些刺眼,便道:“时辰不早,本座也该告辞了。今日叨扰已久,多谢款待。”
石青璇闻言,心中莫名生出一丝不舍,但她性子清冷,不善挽留,只是将那幅画小心翼翼卷起,紧紧握在手中,轻声道:“盟主客气了。今日能与盟主论茶、合奏,又得此神作,青璇受益匪浅,感激不尽。他日有暇,望盟主能再次光临这幽林小筑。”
“一定。”易华伟拱手。
师妃暄也向石青璇告辞。
石青璇将二人送至竹篱外,目送着那一青一白两道身影,沿着来时落满秋叶的小径,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竹林深处。
她独自立于秋风中,良久,才缓缓低头,展开手中的画卷,看着画中那清冷如仙、眉眼间却与自己一般带着淡淡寂寥的女子,玉指轻轻拂过画上的题字,一抹复杂难言的情绪,在她那清澈如湖的心底,悄然荡漾开来。
幽林小筑重归寂静,唯有秋菊依旧,在阳光下静静绽放。
………………
二人离开幽林小筑,沿着来时那条落满秋叶的幽径,踏上了归途。
阳光将两人的影子在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拉长。林间的光线变得柔和,带着几分暖意,却也掩不住深秋傍晚固有的萧瑟。风比来时更凉了些,卷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发出窸窣的轻响。
师妃暄与易华伟并肩而行,沉默了一段路。脑海中依旧萦绕着今日所见种种——那匪夷所思的天地异变与其轻描淡写的化解,那臻至化境的琴艺,那幅神韵天成的画作,以及他与石青璇合奏时那浑然天成的默契。这一切,都让易华伟身上的迷雾愈发浓厚。
她侧首看向身旁青衫磊落、步履从容的男子,他脸上依旧是那副平静无波的神情。
师妃暄斟酌片刻,终是忍不住开口:“易先生觉得……青璇小姐如何?”
她问得含蓄,但意思却明白。是想探知易华伟对石青璇这等人物的观感,是欣赏其才艺,是怜惜其身世,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想法。
易华伟目光平视前方蜿蜒的小径,脚步未曾停顿,闻言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语气平缓听不出什么情绪:
“箫艺通神,气质空灵,是个妙人。”
易华伟的回答简洁到了极点,仅仅是从艺术和气质层面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听不出任何个人情感的偏向,更没有提及石青璇那复杂的身世背景。
师妃暄对他的反应并不意外,却也有些无可奈何。易华伟的心思,深沉如海,根本不是她几句旁敲侧击所能窥探的。转而轻叹一声,语气中带着几分真诚的感慨,将话题引开:
“妃暄今日,方知先生不仅修为深不可测,于茶道、琴艺、丹青之上,竟也有如此超凡脱俗的造诣。每一道,都近乎于‘道’,实乃妃暄平生仅见。先生之才,真可谓……深不见底。”
她这话是由衷而发。易华伟今日展现出的种种才艺,任何一项放在寻常人身上,都足以名动一方,而他却仿佛信手拈来,融会贯通。
易华伟听了,嘴角微微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笑容中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意味,似是自嘲,目光落在道路前方一株叶片几乎落尽、枝干虬劲的老树上,语气带着一种超乎年龄的淡然与…一丝缥缈:
“妃暄过誉了。世间技艺,无论文武,无非‘熟练’二字罢了。沉浸得久了,见得多了,想不‘精通’也难。”
“沉浸得久了?见得多了?”
师妃暄暗自思忖,易华伟看起来不过二十许人,即便从娘胎里开始修习,又能“久”到哪里去?除非……他驻颜有术,实际年龄远非表面所见?或者,他真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际遇,能于短时间内贯通百家?
她自然想不到,易华伟所言非虚。穿越数个世界,累积数百年光阴,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浸淫诸般雅艺;在《笑傲》世界君临天下百年,坐拥四海,收集天下典籍,更有大把时光可供挥霍于这些“小道”之上。
以易华伟历经数个世界磨砺的心智与精神力,学习任何东西都能直指核心,事半功倍。数百年时间,莫说是琴棋书画,便是再偏门的技艺,也足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于他而言,这确实只是“熟练”而已,早已超越了单纯技巧的层面,融入了对“道”的理解。
易华伟没有理会师妃暄的沉思,继续缓步前行。夕阳的余晖为他青色的衣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却丝毫化不开他周身那股仿佛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源自时光长河的疏离感。
师妃暄看着他沐浴在夕阳中的侧影,只觉得眼前之人愈发神秘莫测,心中有无数疑问,却也知道,有些答案,并非急切间可以求得。
就在她准备将诸多思绪暂且压下时,走在前方的易华伟却忽然开口:
“妃暄似乎对本座与青璇小姐的交流颇为关注?”
师妃暄心头微凛,面上依旧维持着平静:“青璇乃妃暄好友,见她能得遇知音,心中亦是为她欢喜。”
“哦?是吗?”
易华伟脚步未停,目光依旧看着前方,语气里却多了一丝若有似无的玩味:“只是观你今日言行,与其说是为好友欣喜,不如说…更似一种审慎的观察与衡量。妃暄,你与石青璇这‘好友’之情,似乎并非那般纯粹简单。”
易华伟微微侧首,眼角的余光扫过师妃暄瞬间凝住的脸庞,淡淡道:“慈航静斋传人,心怀天下是好事。但莫要将这份心思,过多浸染到这般清雅之地,亦莫要……在本座面前故作聪明。”
此言一出,如同暮色中骤然掠过的一丝凉风,让师妃暄身形微不可察地一僵。她张了张口,想要辩解什么,却发现在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眸注视下,任何言辞都显得苍白无力。
易华伟并未动怒,甚至语气都算不上严厉,但那平淡话语中蕴含的洞察与警告,却比任何疾言厉色都更让她心惊。
易华伟收回目光,不再多言,继续悠然前行。
师妃暄默然跟上,心中却波澜起伏,再难平静。(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