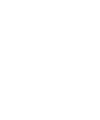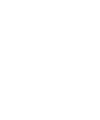黑葫:悟空 - 第28章 杨釗三顾云阳
云阳县衙,杨国忠身著考究的鹿皮靴,每一步都重重地碾过石阶,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到云阳了。回想起离开成都那日,街头算命瞎子摸著他的掌纹,声嘶力竭地喊道“紫薇冲煞”,仿佛是一道紧箍咒。那瞎子断言,若他攀不上驪山宫的青云路,便只能在剑南道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永无出头之日。这预言如同阴霾,一直笼罩在他心头,也让他对此次云阳之行抱有孤注一掷的决心。
在去找县丞的路上,前两次来云阳的经歷如走马灯般在他脑海中浮现,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这让他的心情愈发沉重。
第一次来云阳时,他在客栈里,眯著眼睛,死死地盯著跪在堂下的鸟贩,喉头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压抑著怒火说道:“你说云阳有白鸚鵡,我才从蜀中快马加鞭赶来。如今一句『看走了眼』就想把我打发了?”想起三日前在成都听到信徒传递的消息,说是有波斯胡商带著一只通体雪白的灵禽入蜀,最终停在了云阳县,他满心期待,以为自己终於抓住了命运的转机。
“杨县尉恕罪!”鸟贩嚇得额头重重地磕在青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那鸟贩子原是岭南来的,信誓旦旦地说手头有只雪羽金喙的灵物,谁知前日验货时,笼子里竟变成了一只灰扑扑的鷯哥……”鸟贩的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杨国忠下意识地转头望去,瞥见緋色官袍的一角掠过院墙,几个佩刀的衙役气势汹汹地径直闯进后院。鸟贩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杨国忠的拇指狠狠掐进掌心,留下深深的印记。他认得那緋袍上的银銙,那是京兆府差吏的標誌。果然,后院很快传来锁链拖地的声响,夹杂著岭南口音的哭嚎:“那白鸚鵡早被杨府的人提走了!”听到这话,“萧炅”这个名字在杨国忠脑海中一闪而过,他的瞳孔微微一缩,心中涌起一股不甘与愤怒。他缓缓起身,袖中滑出一枚玉韘。这枚玉韘是三日前从族叔杨玄璬府里顺来的,玉色虽有些浑浊,但在这小小的云阳县,却足够让县衙的胥吏对他这个蜀中县尉多赔几分笑脸。此刻,玉韘贴著掌心,却烫得如同烧不起来的野火,让他心中的烦躁愈发浓烈。
他戴上幕篱,决定必须快人一步,悄悄地把白鸚鵡带走。不久后,他来到一座青瓦朱门的宅邸前,仰头望著匾额上“弘农世泽”四个鎏金大字,嘴角不禁扯出一丝冷笑。在他眼中,这云阳首富杨崇义不过是个旁支末裔,竟也敢打著弘农杨氏的旗號招摇过市。
门房通报时,杨国忠瞥见廊下一只鎏金鸟架闪过雪色残影,他的心跳陡然加快。他故意將腰间鱼袋往前提了提,露出半枚铜符,那是蜀州新都县尉的官凭,在这商贾云集的云阳,足够让那些商人膝盖发软。
“釗弟远道而来,可是为族中祭田之事?”杨崇义捻著沉香木珠,满脸堆笑地迎出来,广袖飘荡间,隱隱透出一股鹰隼粪便的腥气。
“崇义兄说笑了。”杨国忠没有理会杨崇义的寒暄,径直走向廊下,指尖猝然掀开遮在金架上的黑绸。白鸚鵡受到惊嚇,惊鸣一声,翅羽掀起的风里竟挟著龙脑香的清苦。杨国忠瞳孔微缩,眼前的白鸚鵡羽色如崑崙雪般纯净,金喙似佛前灯般耀眼,这般品相,就连宫中驯兽监都难以养出。
杨崇义的木珠声戛然而止,脸上闪过一丝慌乱,隨即说道:“釗弟若喜欢这鷯哥,我让人另挑十只送去蜀州。”
“我要它。”杨国忠的指甲掐进鸚鵡棲木,木屑簌簌落在青砖上,他语气强硬地说道,“听说这畜生能诵《金刚经》?正合为圣人太后祈福之用。为杨家著想,交出来。”他特意咬重“圣人”二字,隨后袖中滑出一页皱巴巴的纸,那是从族妹玉环寄回的家书里撕下的,还沾著驪山温泉宫的硫磺味,他想用这来震慑杨崇义。
暮色渐渐染红了庭院,气氛变得愈发紧张。白鸚鵡歪头盯著两个僵立的杨姓男子,忽地开口:“交出来!交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叫声让杨崇义脸色骤变,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恐。
“三日后我自来接它。”杨国忠翻身上马时,听见身后传来瓷器碎裂声。他抚过袖中躁动的白羽,想起玉环信中那句“圣人为惠妃娘娘斋戒,久不御珍玩”。他心中盘算著,只要他亲手將这只白鸚鵡呈到高力士面前,由高力士掀开笼布的那一刻,世上就会记住是杨釗献上了祥瑞,他也就能藉此机会平步青云。
然而,第二次来的时候,事情依旧不顺利。当他再次来到杨府,刚踏入府门,就被一群衙役团团围住。彼时,县令正在杨府查案,气氛本就紧张压抑。衙役们见杨国忠戴著幕篱,心中一惊,这不就是杨崇义失踪前见过的神秘人吗?当下也顾不得许多,一拥而上,就要將他抓捕。杨国忠本是为了白鸚鵡而来,却被当成嫌犯抓捕,他又惊又怒,他怎么也没想到会遭遇这样的变故,幸亏自己有些武艺,夺路而逃,而这一次,他依旧没能得到白鸚鵡,再次无功而返。
前两次的挫折让杨国忠备受打击,但也让他更加执著。“这一次必须成功!”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儘管空气中瀰漫著硫磺混著腐鼠的气味,可此刻在他看来,竟比成都赌坊的腌臢味道乾净些。
“杨县尉,当真不是下官推脱。”王县丞缩在油污斑斑的公案后,双手不停地將案上的卷宗推了又拢,仿佛那堆黄麻纸能挡住杨国忠刀锋似的目光,“杨崇义暴毙案牵扯京兆府,萧明府三日前亲批的牒文,证物一律不得外提……”王县丞说到“萧明府”时,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仿佛咽下了一枚生铁,脸上满是为难与畏惧的神情。
杨国忠的指尖在案上轻轻叩击,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打破了短暂的沉默。隨后,他袖中滑出一枚错金铜符,这是半月前从蜀王府长史那里贏来的,在这官场中,足够让七品下的小官们膝盖发软。
杨国忠指腹摩挲著铜符错金纹路,这是半月前在蜀王府设的局——他故意让长史在双陆棋局上连贏三把,待对方酒酣耳热时,方掏出那副灌了水银的象牙骰子。此刻铜符边沿还沾著长史倒地时溅上的醒酒汤渍,在烛火下泛著油光。
铜符撞在卷宗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惊飞了梁间的雀鸟,王县丞的瞳孔猛地收缩。
“王明府可认得这符?”杨国忠的声音像浸了油的麻绳,又滑又韧,带著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蜀王殿下听说云阳有祥瑞现世,特命某来查验。还是说……”他忽然俯身,簪头在对方官袍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眼神犀利如刀,“萧京兆的手,已经伸进宗室案牘里了?”
偏堂骤然陷入死寂,只有檐角的铁马被北风撞出细碎的声响。王县丞的指尖在“蜀王”二字上痉挛般地蜷起,他心中明白,眼前这位杨县尉不好惹,可萧京兆的命令也不敢违抗,內心陷入了两难的挣扎。
沉默片刻后,王县丞无奈地起身,说道:“下官……下官这就带县尉去证物房。”慌乱中,他起身时打翻了砚台,墨汁泼在牒文“京兆尹亲查”五个硃砂字上,宛如一团溃烂的疮,似乎也预示著这趟证物房之行不会顺利。
证物房的铜锁“咔嚓”一声打开,王县丞和杨国忠走进屋內,却发现白鸚鵡的鎏金架上空空如也。王县丞脸色一变,赶紧找来蒋索询问白鸚鵡的去向。
廊下传来算筹碰撞的脆响,蒋索腋下夹著半卷鱼鳞册匆匆赶来。这个精瘦胥吏的目光在杨国忠腰间铜符上打了个转,立即堆起满脸褶子:“县丞容稟,那扁毛畜生自打进了证物房,日日啄得金架火星四溅,昨儿还把萧京兆亲批的封条扯成了流苏......”
“少扯閒篇!”王县丞的唾沫星子溅在蒋索鼻尖上,“鸟呢?”
“县令让张仪騫小郎君领去养了,几日没怎么吃喝,怕是要死了。”蒋索回答道。
王县丞揉了揉眼睛,再看时,杨县尉已退至门边,袖口微微晃动,看似如常,可他知道,杨县尉此刻心里定是怒火中烧。“既是將死之物,某便回稟蜀王另寻祥瑞。”杨国忠脸上依旧掛著笑容,拱手时袖中玉韘轻叩铜符,暗记下“张仪騫”这个陌生名字。他转身离开,脚步虽依旧沉稳,此刻最妙手,当属让所有人都以为杨县尉已弃牌离场。可他內心已在盘算著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他绝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这只白鸚鵡,他势在必得……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