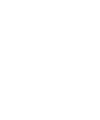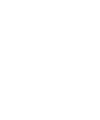大汉:陇西李氏,打造超级家族 - 第227章 曹操激动:“武睿侯竟也挂念着朝堂
随着小黄门宣读太皇太后懿旨,封赐董卓持剑上殿特权、晋相国、总领百官,允陛下称相父的话响彻,朝堂上文武百官一片哗然。
曹操亦是万分震动,忙看向董太皇太后,见其垂着眼帘,似乎滋润了几分,但是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仪。
再看董卓,紫袍玉带衬得那张横肉丛生的脸,此时越发嚣张,嘴角噙着的笑意几乎要溢出来,得意非凡。
“太皇太后,不可啊,岂能如此!”司徒袁隗上前,又惊又怒先是看了一眼董卓,拱手道:
“相国之位自萧何、曹参之后已数百年不设,持剑上殿更是权臣之兆!董卓入京不过数月,何德何能受此殊荣?此旨……恐非您本意吧?”
正欣喜的董卓闻言,猛地转头,铜铃似的眼睛瞪向袁隗:
“袁司徒,你此言什么意思!我董卓,就不能担任相国吗?太皇太后亲笔懿旨,盖着凤印,难道还能有假?咱家诛杀十常侍、平定羌乱,护陛下登基,这功劳难道配不上一个相国之位?”
董卓这个时候自然不肯相让,他已经做好了朝臣不支持的反应,冷哼道:“袁司徒,对老臣吹毛求疵,莫非是看不得大汉有能臣辅政不成?”
“你!”袁隗被董卓的话给噎住,看着与自己针锋相对的董卓,却是感觉这其中必有蹊跷。
太常杨彪这时,也紧随其后,对太皇太后拱手道:
“相国一职总领百官,形同摄政!陛下虽幼,但是,自有太后与朝臣辅佐,何须称异姓为相父?此例一开,国体何在啊?”
黄琬紧随其后,吹胡子瞪眼,对董太皇太后拱手道:
“臣请太皇太后收回成命!!”
“臣等附议!”数十名大臣齐刷刷跪倒,劝谏声一时间几乎要掀翻殿顶。
董太皇太后站在殿中,一时间像一尊泥塑的雕像,听着百官的呼喊,看着他们震惊、不可置信的神色,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已经答应过董卓,要“配合”,要让天下人相信这是她心甘情愿的,不然,董卓若是真要鱼死网破,那么,董氏族人以及刘协等人便都完了。
董太皇太后只觉得喉咙里堵着,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董卓见状,却有些惊怒,他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反对,但是却是明白不可如此下去了,不然真收不了场了。
董卓猛地往前踏了数步,他扫视着跪倒的群臣,眼中凶光毕露:
“一群尸餐味素之徒!咱家为大汉出生入死,难道配不上这相国之位?太皇太后的懿旨在此,你们是想抗旨不成?”
说着,董卓一把夺过小黄门手中的绢帛,高举过头顶:
“看看!上面是太皇太后的凤印!你们质疑咱家,还是质疑太皇太后?又或是质疑大汉的律法?”
“这是太皇太后亲自赐下懿旨,并让小黄门当众宣读,难道有假?”
董太皇太后听着董卓忿怒的话,她哪里不知道,董卓这是逼着她表态,董太皇太后缓缓抬起头,声音干涩道:
“众卿不必多言了,此乃哀家本意!董太尉有功于社稷,辅政亦是应当,哀家身体多有不适,思念先帝,因此,特意提拔董太尉为相国。”
董太皇太后的话响彻,董卓心中大喜。
“太皇太后!”袁逢猛地抬头,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与惊怒,道:“岂能如此……”
“够了!”董太皇太后厉声打断,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道:
“朝堂之事,哀家自有决断。再有非议者,严惩不贷!”
董太皇太后这话一出,群臣彻底愣住了,尽管不可置信,但是那声“严惩不贷”像一把冰冷的刀,架在每个人脖子上。
董卓当即便笑了起来,冷哼道
“都听见了吗?这是太皇太后的金口玉言!从今日起,老臣便是大汉相国!持剑上殿,总领百官!”
说着,董卓在所有人注视下,来到龙椅一侧,看着有些惊慌的小刘协,粗声粗气地道:
“从今以后,陛下也当称老臣一声相父,本相国定能扶持陛下振兴大汉。”
五岁的小刘协听着董卓那粗犷的话,吓得有些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哭出来,怯生生地看向董太皇太后。
“陛下,叫相父吧!”董太皇太后叹息一声,道。
小刘协听董太皇太后的话,也只好对董卓颤抖喊了一声:
“相…相父…”
“哈哈哈,好孩子,好陛下!”董卓高兴,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大手在小刘协头上胡乱揉了揉,大声笑道:
“陛下放心,以后有相父在,谁也不敢欺负你!”
这一幕落在群臣眼里,更是心如刀绞,昔日威严的皇室,如今竟被一个西凉武夫如此拿捏。
曹操咬着牙,一双眼睛瞪大,看着这一幕。
他看着满脸无奈之色,又夹杂着些许无力的董太皇太后,只感觉这其中绝对有问题。
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恼怒声音响起:
“董卓若是你真为大汉着想,便该恪守臣节,而非如此僭越!”
大殿内众人循声望去,只见马日磾站了出来,须发皆白的脸上满是悲愤,指着董卓道:
“董卓你可知,萧何当年虽为相国,却从未敢持剑上殿。霍光辅政,亦不敢让天子称父!你这般作为,竟然还敢揉天子头,与王莽何异?”
董卓脸色骤变,眼中杀机暴涨,大喝道:“马日磾!你敢骂咱家是王莽?”
“难道不是吗?”马日磾挺直了腰板,中气十足道:
“老夫食汉禄四十载,对大汉忠心耿耿,谨言慎行,今日老夫纵是死,也要说句公道话!老夫不知太皇太后为何封你你董卓为相国,但是,汝此举,分明是狼子野心,祸国殃民!”
马日磾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道:“大汉江山岂能容你这等匹夫玷污!”
“老匹夫找死!”董卓被戳中痛处,怒不可遏,猛地从一旁的羽林军身上抽出一把佩剑,寒光瞬间照亮半个殿堂。
董卓此举,瞬间让朝堂文武百官哗然一片。
董卓胆敢当朝杀人不成!!!
“相国息怒!相国息怒!”李儒见状忙拦住董卓,压低声音道:
“今日乃主公荣登相国之喜,斩杀老臣恐失人心,得不偿失啊。”
董卓胸口剧烈起伏,剑刃在阳光下闪着慑人的光,死死盯着马日磾那张毫无惧色的老脸。
他倒是想直接一刀劈了这碍事的老东西,但李儒的话却点醒了他,他刚升任相国掌大权,便擅杀重臣,确实容易授人以柄。
“哼!”董卓最终还是悻悻收剑,剑鞘撞击甲胄发出沉闷的响声,冷哼道:
“老匹夫,念你一把年纪,咱家今日暂且饶你!再敢胡言乱语,本相国饶不了你!”
马日磾却像是没听见他的威胁,依旧挺直脊梁,对着龙椅方向深深一揖:
“太皇太后、陛下啊,还请收回……”
话音未落,马日磾一口气没上来,竟气晕,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马大人!”
“马公!”
袁逢、杨彪、王允等一众人纷纷惊呼着围上去。
董卓看着倒在地上的马日磾,脸上没有半分愧疚,反而冷哼一声:
“不知好歹的东西。”
董卓看着乱成一片的文武百官,大声道:
“从今日起,朝政由本相国总揽!各部奏折先呈相国府,再禀陛下!!”
董卓晋升相国当天便在洛阳城引起了巨大的哗然之声。
但是,对于世家以及袁氏不满,文武百官的弹劾,董卓并不在意。
相反。
成为相国的董卓,彻底撕下了最后一层伪装。
董卓坐上相国之位未满半月,便开始挥舞屠刀,决定在朝堂上立威。
当然,董卓还是刻意绕开了袁氏。
朝堂之上,“清淤”的屠刀首先砍向了无依无靠的谏官。
马日磾当日虽气晕,但是董卓记恨其,并没有放过其。
以“不尊圣意”罪名,直接把其下狱。
随之,董卓又以“查究同党”为名,将三位曾与马日磾联名上书的议郎拖至殿外,西凉兵的刀落得干脆,三颗头颅悬在承天门上,这引起朝堂官员一片哗然与愤怒。
不过,董卓并没有就此罢手,在朝堂上,对于依附自己的官员提拔,对于弹劾自己的官员,如果不是位高权重,或是痛打,或是罢黜,一时间,朝堂上都笼罩在董卓的凶威之下。
袁隗见此情景,与袁逢商议后,最终递上辞呈,称“年事已高,不堪政务”,想回汝南养老。相国府,董卓捏着辞呈看了半晌,终究没敢动这位四世三公的司徒。
袁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真要逼急了,怕是会引火烧身。不过,董卓却是冷笑一声,直接在辞呈上批了“准”,派了三百西凉兵“护送”,名为保护,实为监视。袁隗坐在离京的马车里,掀帘望着洛阳城的轮廓,老泪纵横,一声叹息便离开了。
准了袁隗辞职,董卓转头便提拔了“投向”自己的王允为新的司徒。
朝堂上一时间,真的成了董卓一言堂。
一些官员大臣见董卓毫不吝啬提拔王允为三公,也是纷纷投向了董卓。
清除了碍眼的官员,董卓的奢靡之心如野草开始疯长。
董卓嫌太尉府“格局太小,配不上相国身份”,竟下令拆除洛阳城西三里的民宅,并圈地十里,要建一座“相国府”。
图纸上的宫殿群比皇宫南宫还要气派,主殿“曜德殿”用南海进贡的珍珠镶窗,后园“丽园”引洛水穿园而过,遍植西域传来的奇,还特意造了座“迷仙楼”,说是要“收纳天下绝色,以娱晚年”。
征调民夫的文书贴满了洛阳十二门,上面写着“十五至五十岁男子,皆需服役三月,违令者斩”。西凉兵挨家挨户抓人,敲碎了无数门板,拖走了无数哭喊的壮丁。
城南有户人家,儿子刚娶亲三日,便被抓去修坞,新媳妇追着囚车哭了半里地,被骑兵一鞭子抽在脸上,血流如注。工地上,民夫们日夜不休,饿了啃树皮,渴了喝带着泥沙的河水,稍有懈怠便遭鞭抽。
为了填满修相国府的窟窿,以及增强自己麾下的军队,董卓最终把算盘打到了天下百姓头上。对各州下达命令“加征天下赋税两成”,美其名曰“暂借民力,以固社稷”。
更祸乱大汉民生的是私铸钱币,董卓以五铢钱“太重,不便携带”,命人把洛阳、长安的铜人、铜钟、甚至太庙的铜鼎都熔了,铸造成一种“小钱”,钱身薄得能透光,上面的文字模糊不清,重量还不到五铢钱的三分之一。
这种劣币一流通,市场顿时大乱。商户们宁愿以物易物,也不肯收小钱,百姓拿着一筐小钱,却买不到一升米。董卓却是不管这些,只命西凉兵拿着小钱强买强卖,绸缎庄的锦缎、粮铺的米、酒肆的酒,被抢得一干二净。有粮商哭着求西凉兵“按市价给钱”,被一刀劈成两半。
感觉大权在握的董卓,最终把手伸向了后宫中先皇刘宏的妃嫔。
董卓知道灵帝的妃嫔中有几位容貌出众,直接闯入掖庭,将除了打入冷宫被冯芳派人保护的何太后外,二十余名先帝妃嫔尽数掳至丽园。
其中有位姓周的贵人,是灵帝生前比较宠爱的,抵死不从,骂道:“董卓老贼,你敢辱先帝妃嫔,就不怕天打雷劈吗?”
董卓狞笑着让人把周贵人绑在柱子上,让西凉兵轮流羞辱,直至气绝。其余妃嫔吓得魂飞魄散,只得忍辱承欢,夜里常在园中哭泣,哭声被风吹到宫外,百姓听了无不咬牙切齿。
董卓在丽园里夜夜笙歌,喝到兴头上,便让先帝妃嫔们穿着薄纱跳舞,醉醺醺地指着她们狂笑,道:
“你们这些曾伺候先帝的,如今伺候本相国,是你们的福气!”
这话传到永乐宫,董太皇太后喃喃道:“是哀家引狼入室,哀家对不起先帝啊,大汉……”
小刘协的日子也是越发难捱,董卓每日都要“教导”他,实则把小刘协当成玩物。
有时逼着五岁的小皇帝学西凉话,学不会就不让吃饭,有时喝醉了,把小刘协抱在腿上,满嘴酒气地亲他的脸,嘴里嚷嚷道:
“咱家的好儿子,以后这天下都是你的,当然,你得听相父的话”。
小皇帝吓得夜夜做噩梦,醒来就抱着董太皇太后的脖子哭喊,问道:
“相父为什么那么凶?”
董太皇太后只能抱着他流泪,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朝堂上,曹操看着董卓越发猖狂,把洛阳城胡作非为,心中却是在发冷。
作为大汉九卿之一廷尉,曹操负责掌管天下刑狱,能够接触到更多关于董卓的罪恶事实。
曹操甚至已经知道了董卓把先帝妃嫔掠至丽园,侮辱先帝妃嫔之事。
这日,曹操来到了司徒府,找到了王允。
不过,面对一心痛恨的曹操,王允并没有立即说什么,反而让人请来了卫尉冯芳。
冯芳是李昭的岳丈,如今已经是从羽林军中郎将,提拔被封为九卿之一的卫尉了,尽管只是虚名,并没有多少实权,但是,也是董卓亲封。
北方,李昭拥兵十万兵马,雄据并州,负责镇压救活军并且防备已经占据了漠南草原的夏胡族,再加上李氏子弟李辰同样坐拥幽州,四、五万大军,兵强马壮,李氏并不是谁都能够得罪的。
最让董卓感觉忌惮的是,李儒派细作打探到的消息是救活军首领周开似乎与李昭如今关系相处颇为紧密,彼此经常来往,周开甚至有拜李昭为主的意思。
周开麾下兵马名义上十万,甚至能够鼓动数十万义军,再加上李氏兵力。
这让本来就对李昭忌惮的董卓,愈加的忌惮了。因此,董卓非但不敢动得罪李昭,不敢招惹何太后,甚至董卓为了安抚李昭,还提拔了李昭的岳丈冯芳成为九卿之一的卫尉。
司徒王允府中,大厅内。
曹操略微有些惊疑到来的冯芳,不过,曹操也并没有想太多,毕竟,冯芳是李昭的岳丈,是不可能是董卓的人的。
酒过三巡,宴过五味。
曹操喝的满脸通红,攥着拳头,又饮下一樽酒,终于忍耐不住了,颇为愤恨道:
“司徒、卫尉可知,董卓已将先帝妃嫔掳至丽园?周贵人抵死不从,竟被他让麾下轮流至死……”
话未说完,曹操猛地将酒樽掼在案上,脆响在厅内回荡。
曹操的声音因酒意与怒火而嘶哑,目光扫过王允与冯芳,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道:
“董贼如此悖逆,太皇太后在宫中久不出面,其中必有苦衷,曹操愿往,但是董贼封锁皇宫,阻拦外人面见。”
“当务之急,乃是面见太后,弄清事情原委,二位可能助曹操一臂之力?”
王允面色沉如水,看向冯芳道:
“卫尉在宫中尚有旧部,能否设法让孟德面见太皇太后?”
王允是知道冯芳在宫中是有旧部的,甚至,关押皇后的众羽林军以及侍女便都是冯芳的麾下,在宫中,就连董卓的人都不能靠近。
冯芳闻言,摸了一下腰间的卫尉印绶,沉默片刻,又从袖中取出一枚暗纹木牌,看着曹操,道:
“孟德,武睿侯虽在并州,但也非常关心洛阳局势,武睿侯经常写信交代芳,若是董卓乱政证据确凿,或是朝局有变,王公、孟德皆是忠臣,可以信任,也可全力助之!”
“这是卫尉印绶,这是永乐宫守夜内侍的腰牌,今夜三更,我会令羽林旧部在宫墙西北角接应。只是……太皇太后身边未必干净,孟德当需得万分谨慎。”
曹操、王允听到冯芳的话,当即身体猛震。
武睿侯李昭竟然还关心着朝堂?
甚至说他们二人皆是大汉忠臣,让冯芳全力助之!
曹操顿时就有些激动,道:
“武睿侯真乃大汉忠臣,虽远在边疆,仍然心在朝堂,若是能有武睿侯助力,那么灭除董贼,曹操便有信心了!”
(本章完)
添加书签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